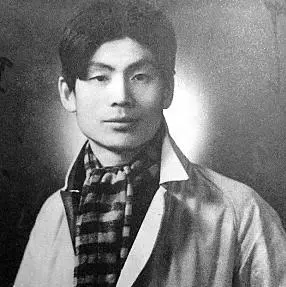说到东北文学,从世纪初的萧红一代,到世纪中迟子建一代,再到80后90后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铁西三剑客”一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东北有一群年轻的作家,他们大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同时也经历了“九一八”事变,目睹了国土沦丧的过程。他们无法接受当亡国奴的命运,纷纷流亡到关内。
“九一八”不仅改变了东北的历史和命运,也改变了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道路,他们将自己的创作融入社会剧变的洪流中,纷纷拿起笔,书写在故乡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重要一笔的东北作家群。他们是由五四新文学过渡到全国抗战文学的桥梁。他们的创作,以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革命性,预告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给东北文学注入了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基因。
“成群或是孤飞的老鸦,掠过人们的顶空,掠过白桦林的高梢,飞向天的一边去。那边是一片宁静的田野,田野的尽处是一带无绵尽的远山……”这段文字出自东北作家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开篇。
“厨房间的边缘钉着一圈狗皮,为的是遮风,因为北方的冬季,就是门缝一隙空,那风吹进来,也会使一天烧三十斤煤的火炉失去热力。”在《混沌》中,骆宾基寥寥数语,就写出了数九寒天里的东北生活的与众不同,以及寒风的野蛮与威力。
今人品读萧红的文学作品,会沉迷于她独有的诗化气质,这种敢于打破传统障壁的精神气质,投射在文学作品上,或许就是鲁迅所说的“越轨的笔致”。鲁迅一直所称颂的,便是要敢于直面生活的惨烈。鲁迅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一文中,称赞萧红刻画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作家陆续到达关内,大致活跃于南北两边。集中于上海的有萧红、萧军、李辉英、穆木天、舒群、高兰、罗烽、白朗、骆宾基、孔罗菰、林珏、耶林等。而北边活跃于北平(今北京)的有端木蕻良、马加、杨晦、于毅夫、丘琴、师田手、刘澍德等。
1932年,李辉英在丁玲主持的左联刊物《北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同时也是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第一篇描写东北抗日救亡的小说《最后一课》。其后数年,作家萧军、萧红写出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舒群写出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写出了以沦陷后的沈阳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第七个坑》;骆宾基写出了表现东北早期抗日游击队生活的小说《边陲线上》;马加写出了《登基前后》;端木蕻良写出了《科尔沁旗草原》等等。
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带给关内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令国人为之震动,引起文坛的瞩目。特别是在当时作为全国进步文化活动中心的上海,他们感受到了上海左联作家们的呵护与关爱,更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大力提携。
鲁迅在为萧军《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序中预言:“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萧红与萧军的抗争精神,反映到创作上,便是从生活真实出发,不加粉饰、无所顾忌的姿态,不加雕琢、随心而至的文字,把残酷、冷漠的场景画面,铺展到读者眼前,这让鲁迅视为知音。鲁迅在两篇序中的文字不仅是对“二萧”作品艺术特质的勾勒,更是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东北作家群乃至东北现代文学的某些共有特质和意义,第一次准确、系统地提炼出东北文学的精神气质。
综合自辽宁日报、钱江晚报等